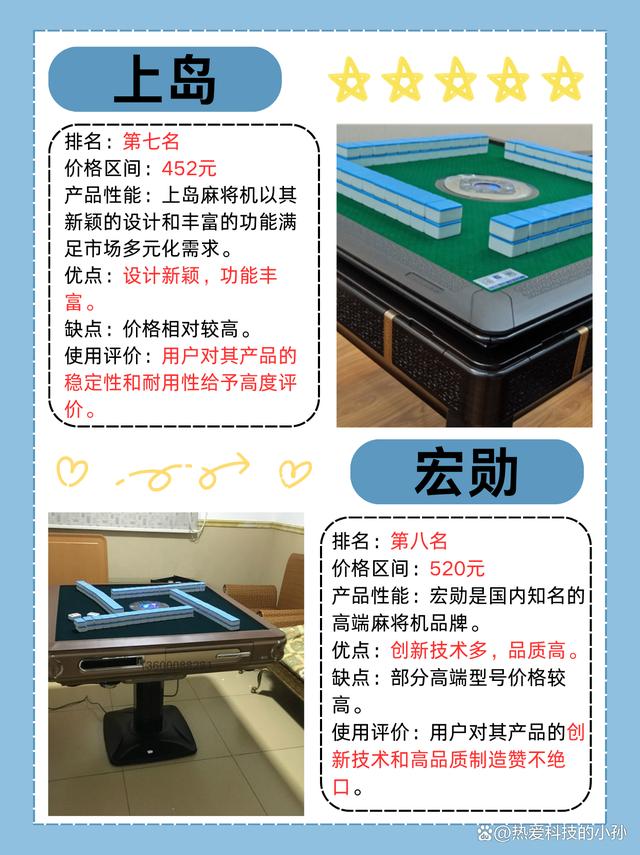麻将机升不起来
麻将机升不起来
人静下来的时候,才发觉那声音原是一直在的——不是麻将洗牌时哗啦啦的、瀑布似的喧腾,而是一种被缚住的、沉闷的嗡鸣,从客厅东南角那台方头方脑的机器肚子里发出来,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里头辗转,被卡住了,使尽了吃奶的力气,也只挣出几声不甘的呜咽,这便是我家那台麻将机,它“升不起来”了,那副本该从幽暗的腹腔里被推送上来、码得整整齐齐的骨牌阵,此刻大约正以一种难堪的姿态,斜躺在某个不上不下的位置,进退维谷。
母亲第一个发现的,她的惊诧里,带着一种近乎天真的不信,又俯身按了一次启动键,绿灯闪了闪,嗡鸣固执地重复着,那光洁的桌面纹丝不动,像一块封死了的墓石。“怪事,”她直起身,拍了拍手上的灰,仿佛那上面沾了什么晦气,“昨儿还好好的。”父亲踱过来,背着手,端详了一阵,脸上是一种老干部审阅文件时的凝重,他没有贸然伸手,只是从喉咙里滚出一声深思熟虑的“嗯——”,然后开始推断,是电路问题,还是升降的滑轨缺了油,他的目光扫过机器的每一个接缝,仿佛能透视进去,找出那粒肇事的、微小的故障。
这麻将机,在我们家落户快十年了,它像一个忠实的、沉默的仪式司礼,见证了多少周末与夜晚的喧嚷,它的升起,意味着一场小型社会活动的开场;它的落下,则宣告着一段亲密或疏离的交谈暂告段落,牌桌之上,是看不见硝烟的战场,也是人情冷暖的试炼场,姑姑的爽利,姨父的精明,老邻居王伯的谨慎,都在那一拿一放、一吃一碰间显露无疑,母亲常说,这四方城里,能看清一个人的脾性,可如今,这城门的吊桥卡住了,我们这些城里城外的“兵卒将帅”,便忽然失了凭依,有些手足无措地围在“故障”的城池边。
我找来螺丝刀,在父亲的指挥下,试图卸下四周的挡板,螺丝旋开,一股微温的、带着淡淡尘埃和机器润滑油特有的、近乎金属的气息,扑面而来,这是我第一次如此“解剖”它,平日里,它被桌布、茶杯、果盘和人们的谈笑装点着,是客厅里一个体面的、功能性的存在,它袒露着内里:纵横的线缆像纠缠的肠子,灰绿色的电路板沉默着,几个小小的电机和齿轮组暴露出来,其中一个齿轮的齿,与一条传送皮带的凹槽,死死地咬合在一处,旁边散落着几粒极小的、白色的塑料碎屑——大约是从某个磨损的部件上崩落下来的。
就是这里了,不是什么高深的难题,只是一次小小的、机械的“罢工”,父亲拿来一点润滑油,我小心地滴在那干涩的咬合处,然后用螺丝刀柄轻轻别了别,咯噔一声,极其轻微,但那紧绷的力似乎松动了,再按下开关,那呜咽的嗡鸣声调忽然一扬,变得顺畅了些,桌面下方传来熟悉的、骨牌被推搅的声响,紧接着,那块厚重的桌面,终于缓缓地、平稳地升了起来,四排长城般的骨牌,完好地出现在我们眼前。
母亲“哎呀”一声,笑了起来,那笑声里有一种重获宝贝的轻松,父亲也点点头,脸上露出满意的、近乎工程师般的表情,他们张罗着要摆开阵势,“试试手气”,然而我,看着那复原的、光洁如初的桌面,心里却并无太多喜悦,方才那番短暂的“解剖”,让我窥见的,似乎不止是几枚齿轮与皮带。
我想起那些牌桌上永无休止的循环,一样的开局,一样的规则,有人赢,便有人输;今晚的春风得意,可能是明晚的铩羽而归,我们追逐着那随机降落的运气,在“碰”、“吃”、“杠”的脆响与“和了”的宣告中,经历着微型的狂喜与沮丧,那麻将机周而复始的升起、落下,不正像这循环的具象么?它提供欢愉,也制造焦虑;它联结我们,也在那方寸的竞争间,划下微妙的心防,它从不疲倦,疲倦的是沉溺其中的人,它今日的“升不起来”,像一次意外的休止符,强行截断了那令人昏昏然的旋律。
我们沉迷于让一切“升起来”——事业要上升,股价要上升,生活的种种指标要上升,就连娱乐,也要轰轰烈烈,要即刻的反馈与输赢的刺激,这麻将机的升起,何尝不是这种集体心绪的一个微小注脚?我们害怕沉寂,害怕无事发生的平淡,于是用一轮又一轮的“开局”来填满时间,用那虚拟的“战果”来确认自身的存在与欢愉,仿佛只有那桌面升起来,骨牌哗然作响,日子才算被“启动”,才有了热络的滋味。
它虽然修好了,随时可以再度轰鸣,但我忽然觉得,那卡住的时刻,或许比它顺畅运转时,更值得倾听,那声挣扎的呜咽,是一个被我们过度使用的器物的叹息,或许,也是一面镜子,照见我们自身某种不易察觉的困顿——在追逐无穷尽的“升起”时,我们是否也把自己卡在了某个欲求的齿轮里,磨损着,却忘了为何而转?
夜又深了些,父母在客厅里,新的一局已然开场,熟悉的洗牌声如同潮水,我走回自己房间,将那充满人声与牌响的热闹关在门外,忽然觉得,有时让那麻将机,或者说,让我们生活里某些轰鸣不息的东西,暂时“升不起来”,就那么静静地卡一会儿,容一些空白与沉默渗透进来,或许并不是一件坏事,故障,也可能是生活给予的一次意外的、深长的呼吸。